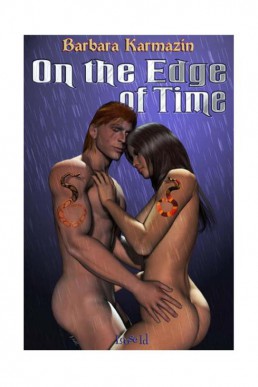
On the Edge of Time
Here there be dragons. On the edge of time, in the wicked twists of wyrmhole space, wyrmdragons pre
Uncategorized [苏]所罗门•伏尔科夫 记录并整理; 叶琼芳 译 46 2nd Feb, 2021
内容提要 本书(原名 《见证》)是肖斯塔科维奇生前口述,由其学生伏 尔科夫记录整理,带到西方出版的, 肖氏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作曲家•他在本书中回顾了自己一生 的坎坷历程,对其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作了深刻的说明,涉及到 苏联文艺界的若干内情,并生动地叙述了文培乃至政界的许多名 人轶事. 本书可作为了解苏联现代史尤其文艺界情况的参考读物.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原版本封面介绍 .《见证》的成书和问世过程极富于戏剧性。俄国人把音乐界 巨'人——季米特里•肖斯塔科维奇作为他们文艺理想的化身介 绍给世界,他在这些回忆录中揭示出他是一个深受苦难的人 ——对他自己和他所扮演的角色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心情。 在肖斯塔科维奇逝世前四年左右,先是在列宁格勒,后来 在莫斯科,苏联富有才华的年轻的音乐学家所罗门•伏尔科 夫,勾起了肖斯塔科维奇对往事的回忆。作曲家终于把发表这 些回忆录视为自己的义务。他对伏尔科夫说:“我必须这样 做,必须。”伏尔科夫记下了这些往事,然后加以整理、编 辑,始终保留肖斯塔科维奇回忆时所特有的风格以及他的跳跃 式的语气。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工作后,肖斯塔科维奇通读了 全书,表示同意,并且逐章签了宇,他同意将稿送到西方出 版,唯一的条件是:到他逝世后才能公诸于世。 肖斯塔科维奇把这些回忆称为“一个目击者的见证”.,把 目击者的直觉贯穿于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回忆,其范围包括他 整个一生,从革命前一直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以后的不幸的 解冻时期。一幕幕情景跃然纸上,使读者有身历其境之感s与 斯大林的令人吃惊的勇敢的谈话> 喧嚣一时的创作新国歌的竞 争(在其中肖斯塔科维奇与哈恰图良是合作者);假夭才的伪 造J剽窃行为的普遍存在。他回想了他所认识的音乐家、艺木 家和作家:普罗科菲耶夫、斯特拉文斯基、格拉袓诺夫、梅耶 纛尔德、阿赫玛托娃和莫他许多俄罗斯文化的中心人物。他愦 懣地谈到在社会各阶层菱延的反犹太主义。他辛辣地描写了随 着掌杈者的调子跳舞的人们,其中有达官贵人,也有无名之 过去,这一切他从未向人公开过,如今,本书所揭示的一 位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在苏联如何度过一生的情景是动人的, 而且往往令人黯然神仿。 . 在感情上,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生活和艺术。这些回 忆的语言朴素、坦率、辛辣、有力一介绍了一个世人从来没 有看到过的肖斯塔科维奇和一个人的功成名就而又可悲可叹的 一生。 序 我和肖斯塔科维奇的私交开始于1960年,即我第一个在列 宁格勒报纸上评论他的《第八四重奏》首次公演的时候。当时, 肖斯塔科维奇五十四岁。我十六岁。我是他狂热的崇拜者。 在俄国学音乐,不可能不从童年时期就听到肖斯塔科维奇 的名字。我记得,在1955年,我的父母从一次室内音乐会回来 时极为激动,原来是肖斯塔科维奇和几位歌唱家第一次潢出他 的《犹太组歌》。在一个刚受到反犹太主义的恶浪冲击的国家 里,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居然敢于公幵发表一部用怜悯和同情为 犹太人执言的作品。这是音乐界的大事,也是社会的大事。 我就是这样开始知道了这个名字。我接触他的音乐是在几 年之后。- 1958年9月,叶甫根尼•莫拉文斯基在列宁格勒音乐 厅指挥肖斯塔轉维奇的《第十一交响乐》。这首交响乐(写于 1956年匈牙利暴动之后)表现了入民,表现了统治者,有时并 列地表现这两者;第二乐章以自然主义的真实手法粗厉地描写 无自卫能力的人民如何被屠杀。令人震动的诗篇。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在离开音乐会时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。直到今天, 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对于我的主要的力量所在。 我全神贯注地研究我所能得到的肖斯塔科维奇的所有乐 谱。在图书馆里,歌剧《姆岑斯克的麦克白夫人》的简化钢琴谱 已经被悄悄地收走了。我要获得特别许可才能够取到第一钢琴 奏鸣曲的乐谱。早期的“左倾”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仍在正 k禁止之列。在讲授音乐史的课上和在教科书里,他仿査到诽 谤。年轻的音乐家三三两两秘密地聚到一起研究他的音乐。 每逢他的作品首次公演,总要在报界、音乐界和权力的阶 层引起一场或明或暗的斗争。肖斯塔科维奇会站起来,很不自 在地走到台前答谢听众的高声欢呼。我的偶像会从我身旁走 过,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小脑袋着意地保持着平衡。他显得极为 孤单无力,我后来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。我满心希望尽我 所能地去帮助他。 在《第八四重奏》首次公演后,我有了说出自己心情的机 会。这是一首不同凡响的作品,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音乐自 传。I960年10月,报纸上登出了我的欣喜溢于言表的评论。肖 斯塔科维奇看到了这篇文章:他一贯仔细阅读对他的首次公演 的作品的评论。别人向他引见了我。他说了一些客气话,我如 同到了九重天。在此后的几年内,我又写了几篇关于他的音乐 的评论。这些文章都发表了,在当代音乐的进程中或大或小地 起了作用。 我认识肖斯塔科维奇的时候,大概正是他对自己最不满意 的那几年。人们可能得到一种印象,觉得他正试图疏远自己的 音乐。我开始明白他的处境的内在的——不是外在的——悲 剧,是在1965年春季我协助组织一次肖斯塔科维奇音乐节的时 候。这是在列宁格勒,这位作曲家的出生地,第一次举行这类 音乐节;演出了交响乐、合唱曲和许多室内乐作品。在相当华 丽的旅馆房间里,我和肖斯塔科维奇谈到与音乐节有关的活 动。他显然感到紧张,在我问及他最新的作品时他避而不谈。 他带着勉强的笑容说,他正在为卡尔•马克思的传记影片谱 曲。说了这一句之后他又静默了,一个劲儿在桌上弹着手指。 这次音乐节中肖斯塔科维奇唯一表示赞同的是演出他学生 的作品的那一晚专场。他明显地暗示,关于它的重要性,我必 须同意他的意见。不服从是不可能的。我开始研究他的学生的 音乐,埋头看手稿。有一份手稿特别吸引了我:维尼阿明•弗 莱施曼的歌剧《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》。 弗莱施曼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上过肖斯塔科维奇的课。当前 线移到列宁格勒时,他参加了志愿旅。志愿旅的男儿们是注定 了要为国捐躯的,几乎无一生还。弗莱施曼没有留下坟墓,除 《罗特_尔德的小提琴》外,也没有遗下任何乐谱。 这部歌剧取材于契诃夫的一篇故事,充满着令人悬念的未 了之情。据说,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建议下,弗莱施曼已开始谱 写一部同名的歌剧。在他奔赴前线之前,据说他已完成了简化 谱。现在研究者所能得到的只有总谱,自始至终是以肖斯塔科 维奇特有的潦草的笔迹写的手稿。肖斯塔科维奇坚持说他只不 过为他已故的学生的作品写了配器。这部歌剧是非凡之作,明 净、细腻。契诃夫又苦又甜的抒情的语言以一种可以形容为 “成熟的肖斯塔科维奇”的风格再现了。我决定,《罗特希尔 德的小提琴》必须搬上舞台。 当然,没有肖斯塔科维奇,这件事我是办不到的> 他以一 切可能的方式给予协助。1968年4月首次演出时,他不能到列 宁格勒来,由他的儿子——指挥马克西姆代表他来了。这次演 出引起了轰动,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成功,评价极高。一部不同 凡响的歌剧在舞台上诞生了,随之还涌现了一个新的歌剧院 ——室内歌剧实验剧院。我担任这个在苏联还是首创的歌剧院 的艺术指导。首次演出的一个星期前,我刚满二十四岁。 于是,文化部门的主管者们谴责我们所有人为犹太复国主 义者t可怜的契诃夫,可怜的弗莱施曼。他们的决议写道: “上演这部歌剧是为敌人肋烕。”这意味着这部作品无可挽救 的终了。这对肖斯塔科维奇和我都是一次挫折。他在失望中写 信给我:“但愿弗莱施曼的<小提琴》最终能得到它应有的承 认。”但是,这部歌剧从此再也没有上演。 对于肖斯塔科维奇,《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 > 象征了没有治 愈的罪过、怜俩、骄傲和愤怒,因为不论是弗莱施曼还是他的 作品,都再也没有复活。这次挫折使我们彼此靠近了。当我开 始写作一部关于列宁格勒青年作曲家的书时,我写信请肖斯 塔科维奇为此书写序。他立即回信说* “我将很高兴和你见 面”,并提出了时间和地点。一位著名的音乐出版家同意出版 这本书。 按照我的计划,我希望肖斯塔科维奇写写这些年轻的列宁 格勒人与彼得堡学派之间的联系。在我们见面时,我开始和他 谈起他的青年时代,但是最初遇到了一些阻力。他宁可谈他的 学生们。我不得不耍手段:一有机会我便提出一些对比,勾起 他的联想,使他想起种种人和事。 肖斯塔科维奇让步了,而且超出我的愿望。他终于向我谈 到了旧音乐学院时代,谈到的事情非同一般。过去我所读到 过或者听到过的一切就象一幅已褪色到不可辨识的水彩画。 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犹如一幅幅草草几笔便神态逼真的铅笔素 描——轮廓清晰,特点明确。 我从教科书上熟悉的一些形象,在他的叙述中失去了情感 的光轮。我情如潮涌,肖斯塔科维奇也是如此,虽然他自己并 没有意识到。我没有料到会听到这样一些事情。在苏联,最难 得和最可贵的毕竟是“回忆”。它已被践踏了数十年;人们知 道比记日记或写信更妥当的办法。当三十年“大恐怖”开始的 时候,受惊的公民销毁了私人的文字记录,随之也还抹去了他 们对往事的回忆。此后,凡是应该作为回忆的,由每天的报纸 来确定。历史以令人晕眩的速度被改写。 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。这么多的人在我面前走过 去了,这些行尸走肉,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 事件——而且仅仅以官方许可的方式。 我原以为肖斯塔科‘维奇只是在音乐中直率地表达自己。 我们全都看到过官方报刊上那些把他的名字放在最末位的文 章。*凡是音乐家,谁也不看重这些夸张的、空洞的宣言。人 们在比较亲密的圈子里甚至能告诉你哪篇文章是作曲家协会的 哪位“文学顾问”拼凑起来的。一座纸糊的大山搭起来了,几 乎把肖斯塔科维奇这个人埋在底下。官方的面具紧紧地套在他 的脸上。 因此,当他的脸从面具后面小心翼翼地、疑虑重重地露出 来的时候,我是那样地吃惊。肖斯塔科维奇说话很有特点一 句子很短,很简明,经常重复。但这是生动的语言,生动的情 景。显然,作曲家不再自我安慰地认为音乐可以表达一切,不 需要言词的解释了。他这时的作品以越来越强的力量只说一件 事I迫近的死亡。在六十年代后期,官方报刊上发表的肖斯塔 科维奇的文章是劝他最热爱的听众不要认真倾听他的作品演 奏。当最后的门即将在他身后关上时,还有谁愿意去听它呢? 我写的那本关于列宁格勒青年作曲家的书在1971年出版 了,立即销售一空。(直到我1976年离开苏联的时候,这本书 在全国是讲授当代苏联音乐的教材。)肖斯塔科维奇的序言被 * 有许多次弁没有请肖斯塔科维奇签名,因为这种形式被认为是不必要 -的^反正,谁能怀疑肖斯塔科维奇不会像所有其他苏联公民一样奉承领 袖和导师呢?于是,1950年9月30日的(文学报》上出现了吹捧“斯大林同 志的丰功伟绩”的文章,署名季•肖斯塔科维奇。这篇热情的颂词他本 人连薄都没看过. 严加删节,只留下了谈当前的部分——没有往事的缅怀。 这是最后的强大动力,激励他把他自己在半个世纪里看到 的在他周围呈现的事情告诉世界。我们决定把他对这些事情的 回忆整理出来我必须这样做,必须”他常常这么说。他 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:“你必须把已经开始的事情继续下 去。”我们越来越经常地见面和交谈。 为什么他选中我呢?首先,我年轻,肖斯塔科维奇希望在 年轻人面前——甚于在其他任何人面前——为自己辩护。我热 爱他的音乐,也热爱他的为人,我不编造故事,我不夸耀他对 我的善视。肖斯塔科维奇喜欢我的作品,也喜欢我写的关于年 轻的列宁格勒人的书,曾几次给我写信提到它。 他往往在往事如潮涌上口头时一吐肺腑,但是这种回忆的 愿望需要不断加以酝酿。当我向他谈起他已故的朋友时,他惊 异地听我讲到他已忘却的人和事。“这是新的一代中最聪明的 人”,是他对我的最后评价。我在这里重述这些话不是出于虚 荣,而是想要解释这个复杂的人物是怎样作出这个困难的决定 的。多少年来,他一直觉得往事已经永远消逝了。至于往事的 确还存在一份非官方的记录,这种想法他还需要逐渐习惯。 “难道你认为.历史不是娼妓吗? ”有一次他这样问我。这个问 題流露了一种我还不能领会的绝望的.心情;我所相信的正相 反。而这一点在肖斯塔科维奇看来也是重要的。 我们就是这样合作的。在他的书房里,我们一起在桌旁坐 下,他请我喝一杯(我总是拒绝)。于是我开始提问题,他回 答得很简短,而且,开始时还很勉强。有时我不得不用不同的 方式重复同样的问题。肖斯塔科维奇的思潮需要时间才能奔 放。 渐渐地,他苍白的面容添上了血色,他激动起来了。我继 续提出问题,用速记法记笔记,那是我在当新闻记者的几年里 学会的。(由于多种原因,我们放弃了录音的想法。主要是因 为肖斯塔科维奇在话筒前十分拘束,如兔子在蛇的逼视下似 的。这是他对奉官方之意发表广播讲话的条件反射。) 我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帮助肖斯塔科维奇解除拘束,使他 在讲话旳时候比对知心朋友谈话还要自然:“不要回想你自 己;谈谈别人吧。”当然,肖斯塔科维奇是要回想他自己的, 但是他是从谈别人而及于自己,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映 像。这种“反映方式”是水上城市彼得堡的特征,它闪烁萁 光,隐隐绰绰。这也是安娜•阿赫玛托娃爱用的方式。肖斯塔 科维奇尊敬阿赫玛托娃。他的寓所里挂着她的画像,是我送给 他的礼物〇 • 起先,我们在列宁格勒附近肖斯塔科维奇的别墅里会面, 作曲家协会在那里有一片休养地。肖斯塔科维奇要休息时便到 那里去。那地方不是太方便,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很慢,每次重 新捡起话题不易在情感上适应。1972年我迁到莫斯科在苏联主 要的音乐杂志《苏联音乐》任职,工作很快就顺利地前进了。 我担任了《苏联音乐》的髙级编辑。我易地任职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更接近肖斯塔科维奇,他的住所与这个杂志社在同一座 房子里。尽管肖斯塔科维奇经常离开这个城市,但是我们还是 可以经常会面。*工作的开始总是由他打电话给我——经常是 在清早,办公室里还没有人的时候,他的生硬的、嘶哑的男高 * 除了我们的主要工作外,我也帮他办了许多次要的但繁重的亊务。肖斯 塔科维奇是<苏联音乐>编辑委员会的委员,所以他得要为提请发表的稿 件写评语。在某个音乐问題上有争论时,人们常要求他的支持。在这种 情况下,我便起他的助手的作用,按照他的要求准备评语、答复和信 件。这样,我就成了肖斯珞科维奇和杂志总编辑的中间人。 音问道* “现在你有空吗?能来吗? ”于是,接连几小时令人 筋疲力尽的谨慎的探索开始了。 肖斯塔科维奇回答问题的方式别昊一格。有些措辞显然是 经过多年推敲的。显而易见,他在摹仿他在文学界的偁像和朋 友——作家米哈伊尔•左琴科,一位语言精炼的讽刺叙事文体 大师(他文笔之细腻和穿珠般的精巧是译文所无法表达的)。 果戈里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布尔加科夫以及伊尔夫和彼得罗夫 的语言在他的谈话中经常出现。口中吐出讽刺性的语句时,面 夸却不带一丝笑意。相反,当激动的肖斯塔科维奇开始深深触 _心弦的谈话时,他的脸上露出了神经质的笑容。 他常常自相矛盾,那时就需要猜测他的话语的寘正含意, 拨开假象找到真相需要用毅力同他的紊乱的头绪作斗争。我常 常在离去时筋疲力尽。速记本越堆越高,我一次又一次地阅 读,试图从潦草的铅笔字迹中间组织一部我知道巳经初具规模 的、形象众多的作品, 我把素材分成可以联贯起来的几个部分,按我认为适当的 方式组织在一起,然后拿给肖斯塔科维奇过目。他同意我的写 法。这巳形之于笔墨的情景显然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我逐 渐把这些浩浩瀚瀚的回忆按我的意思整理成章节段落,然后 用打字机打印。肖斯塔科维奇看过以后在每一部分后面都签了 字。 我们两个人都明白,这部定稿在苏联是不可能出版的;在 这方面我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。我采取措施把原稿送往西方。 肖斯塔科维奇同意了。他唯一坚持的是,这本书要在他死后发 表。“在我死后,在我死后,”他经常说。肖斯塔科维奇不想 再经受新的磨炼了,他太虚弱了,疾病已消耗尽了他的精力。 1974年11月,肖斯塔科维奇丨约:我去他家。我们谈了一会 儿,然后,他问我手稿在哪里,“在西方,”我回答,“我们 的协议生效了,”肖斯塔科维奇说:“好的。”我告诉他,我 要准备一项声明,大意是说他的回忆录必须在他死后才能付印 (后来我给他送去了关于这个协议的信件)。在我们谈话结束 时,他说他要送我一张题词的照片。他写道《 “亲爱的所罗 门•莫依谢耶维奇•伏尔科夫留念。季•肖斯塔科维奇赠于 1974年11月13日。”在我准备离去时,他说:“等一等。把照 片给我。”他又加上了一句:“以志我们关于格拉祖诺夫、左 琴科、梅耶霍尔德的谈话。季•肖。”写完后,他说,“这能 对你有所帮助。” 在这之后不久,我向苏联当局申请离境去西方。1975年8 月,肖斯塔科维奇逝世了。1976年6月我来到纽约,决定发表 这本书。感谢那些有勇气的人们(我甚至不知道其中有些人的 名字),是他们把这份原稿安全地、完整地带到了这里。我自 从来到这里以来一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的支持, 并在1976年担任了这个研究所的副研究员。和研究所里的同事 们的接触对我来说得益匪浅。哈珀和罗出版公司的安•哈里斯 和欧文•格莱克斯立即接受了这部稿子。对于他们的建议和关 心,我表示谢意。我的委托律师哈里•托尔希内尔给了我莫大 的帮助。 最后,感谢你,我那在远方的、仍不得不隐匿你的名字的 朋友:没有你始终如一的关心和鼓励,这本书是不可能存在 的。 所罗门•伏尔科夫 1979年6月,于纽约